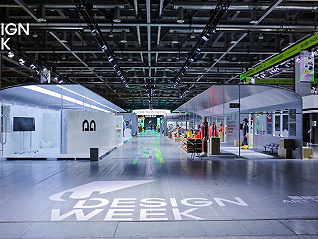糖心logo官網?_國產精彩AV_.手.動.輸.入.網.址.聯.系.客.服.人.員.lanan_shell
對話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航空法研究所執行所長 劉浩 《法制日報》記者 任雪 對話動機 一段時間以來,“低空開放”、“開放低空領域”、“低空空域開放”等概念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一方面,不斷有人提出適度開放低空,以滿足正在迅速發展的私人飛機市場的需求;一方面,也有公眾擔心,放開低空,是否會增加一些不可預知的安全隱患。 近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舉辦的第三屆航空法國際會議上,不少航空法領域的學者對我國目前航空領域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其中不乏對低空空域管理的討論。我國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如何進行?需要怎樣的法律支持?《法制日報》記者就此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航空法研究所執行所長劉浩展開對話。 對話 記者:近年來,隨著經濟水平的發展,私人飛機的擁有量在不斷增加。目前,我國對低空空域的管理情況如何? 劉浩:截止目前,我國私人飛機的擁有數量仍然很低,通用航空器,包括熱氣球、飛艇等總數量剛剛突破1000架。而在美國,這個數字是23萬。1000架背后隱藏的是巨大的消費和市場需求。 對于低空空域飛行,我國有飛行基本規則、《通用航空飛行管制條例》、《民用航空使用空域辦法》、《一般運行和飛行規則》、《中國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規則》等法規予以規范;低空空域飛行的主要問題是目前的管理方式還比較粗放,不夠精細,缺乏靈活性。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意見出臺前,低空空域被作為管制空域管理,導致低空飛行的空域審批環節多、時限長,影響了低空飛行運行的效率,同國外航空發達國家差異比較大,差距也比較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部分通用航空飛行器的擁有和運營單位鋌而走險,出現了違法違規飛行。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時常發生違法違規的“黑飛”現象。有人認為,“黑飛”時有發生,原因在于對違法飛行的懲罰不夠,違法成本低。 劉浩:目前對私人飛機,或者叫通用航空違規非法飛行的懲罰,主要規定在民用航空法第二百零七條、飛行基本規則第一百一十八條和《通用航空飛行管制條例》第四十一條和第四十二條。處罰措施包括吊扣執照1至6個月,停飛1至3個月,罰款2至10萬元。我們說違法成本低,主要是從罰款數額上來說的。 不過,盡管對違法行為的罰款數額不高,但個人認為導致“黑飛”的根本原因并非違法成本低,而是合法飛行的渠道不夠暢通,審批時限偏長,審批權限不清;加上監控手段還不是非常完善,擁有私人飛機飛行的個人在當地往往也有包括財力在內的各種影響力,執法人員也偶有徇私情節,未能“違法必究”,導致違法飛行近年來比較突出。 解決“黑飛”的途徑在于疏導,而不是提高違法成本;過分強調對違規飛行單位和個人的嚴懲并不一定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還會助長腐敗。改革低空空域管理體制,簡化審批程序,提高審批效率,加強低空空域飛行保障,才是解決問題的方向。 隨著國務院、中央軍委《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意見》的出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法》立法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國民經濟“十二五”發展規規劃“改革空域管理體制”任務的設定,相信國家會考慮修改《通用航空飛行管制條例》,并制訂我國的空域使用管理法規。 記者:目前,也有人擔心,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后,私人飛機的飛行會增多,是否會出現私人飛機墜毀事件?如何利用法律盡量避免這種現象的出現? 劉浩:空域的分類和劃分是一項技術性比較強的工作,空域的類別及四維邊界的劃定相互關聯,必須統籌、科學規劃,不能簡單地認為劃出低空空域就能實現通用航空的發展和私人飛機的自由飛翔,通用航空的發展和繁榮是系統的工程。 空域管理體制的改革已經列入國民經濟“十二五”發展規劃,希望在國家空管委的領導下,盡快研究制訂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空域管理體制、機制,并通過立法體現、鞏固改革成果。但是,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考慮到我國國土防空形勢和我國現有空域監視能力,因此改革目標的實現過程應當是審慎的、有步驟的。 私人飛機墜機事件不僅給機上人員帶來傷害,還可能給地面、水面上的第三人和環境造成損害,必須加強飛行的安全管理和損害賠償制度。在安全管理方面,法律能夠做的主要包括:嚴格航空器適航管理和飛行執照管理;制訂適當的通用航空經營審批和非經營性登記制度;修改完善飛行規則;明確管制部門、空防部門、其他服務保障部門和飛行人員之間的責任分工;健全事故和事故征候調查機制;嚴肅違法違規飛行處罰制度。在損害賠償方面,法律一方面要將通用航空的第三人損害賠償保險列為強制保險,另一方面還要建立并不斷完善第三人損害賠償保險理賠制度與程序。 記者:有觀點認為目前我國航空領域的法律缺乏支架性法律,這嚴重制約了我國航空業的發展,您對此怎么看? 劉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非常重視各行業領域的支架性法律,盡管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建成,但在航空領域仍然存在著支架性法律的缺失。由于缺乏能夠統一調整國家航空(包括軍事、海關、警察和其他國家勤務飛行)和民用航空的支架性立法,許多航空領域的深層次矛盾無法解決,或者說無法根本、徹底解決,例如航空管理機構、空域管理體制等,諸多矛盾的解決往往取決于部門協調和領導批示,制約了我國航空事業的發展。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法》歷經4年,已經形成了兩個較為成熟的版本,并進行了大范圍的調研和意見征求。據了解,今年年初召開的國家空管委全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法》草案進行了審議,有關機構正在按照空管委全會的決策積極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法》的立法進程。 記者:您在前面提到,美國的通用航空器達23萬架,在像美國這樣通用航空比較發達在國家,有哪些立法管理經驗可以借鑒? 劉浩:首先,國外對私人飛機并非完全放開,也有嚴格的適航、飛行計劃批準制度,就連通用航空最發達的美國在“9·11”之后也開始反思和調整其通用航空的管理制度。 在通用航空比較發達的國家,空域實現了功能導向性的分類管理,采取了靈活調配的機制,飛行計劃的審批制度設計較為合理,凸現了管理的高效和人性。 目前我國的空域分類、劃設和管理制度以及通用航空的飛行管制改革,包括大家最關注、曝光頻率最高的“低空空域管理改革”,都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航空法研究所執行所長 劉浩
《法制日報》記者 任雪
一段時間以來,“低空開放”、“開放低空領域”、“低空空域開放”等概念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一方面,不斷有人提出適度開放低空,以滿足正在迅速發展的私人飛機市場的需求;一方面,也有公眾擔心,放開低空,是否會增加一些不可預知的安全隱患。
近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舉辦的第三屆航空法國際會議上,不少航空法領域的學者對我國目前航空領域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其中不乏對低空空域管理的討論。我國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如何進行?需要怎樣的法律支持?《法制日報》記者就此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航空法研究所執行所長劉浩展開對話。
記者:近年來,隨著經濟水平的發展,私人飛機的擁有量在不斷增加。目前,我國對低空空域的管理情況如何?
劉浩:截止目前,我國私人飛機的擁有數量仍然很低,通用航空器,包括熱氣球、飛艇等總數量剛剛突破1000架。而在美國,這個數字是23萬。1000架背后隱藏的是巨大的消費和市場需求。
對于低空空域飛行,我國有飛行基本規則、《通用航空飛行管制條例》、《民用航空使用空域辦法》、《一般運行和飛行規則》、《中國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規則》等法規予以規范;低空空域飛行的主要問題是目前的管理方式還比較粗放,不夠精細,缺乏靈活性。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意見出臺前,低空空域被作為管制空域管理,導致低空飛行的空域審批環節多、時限長,影響了低空飛行運行的效率,同國外航空發達國家差異比較大,差距也比較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部分通用航空飛行器的擁有和運營單位鋌而走險,出現了違法違規飛行。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時常發生違法違規的“黑飛”現象。有人認為,“黑飛”時有發生,原因在于對違法飛行的懲罰不夠,違法成本低。
劉浩:目前對私人飛機,或者叫通用航空違規非法飛行的懲罰,主要規定在民用航空法第二百零七條、飛行基本規則第一百一十八條和《通用航空飛行管制條例》第四十一條和第四十二條。處罰措施包括吊扣執照1至6個月,停飛1至3個月,罰款2至10萬元。我們說違法成本低,主要是從罰款數額上來說的。
不過,盡管對違法行為的罰款數額不高,但個人認為導致“黑飛”的根本原因并非違法成本低,而是合法飛行的渠道不夠暢通,審批時限偏長,審批權限不清;加上監控手段還不是非常完善,擁有私人飛機飛行的個人在當地往往也有包括財力在內的各種影響力,執法人員也偶有徇私情節,未能“違法必究”,導致違法飛行近年來比較突出。
解決“黑飛”的途徑在于疏導,而不是提高違法成本;過分強調對違規飛行單位和個人的嚴懲并不一定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還會助長腐敗。改革低空空域管理體制,簡化審批程序,提高審批效率,加強低空空域飛行保障,才是解決問題的方向。
隨著國務院、中央軍委《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意見》的出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法》立法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國民經濟“十二五”發展規規劃“改革空域管理體制”任務的設定,相信國家會考慮修改《通用航空飛行管制條例》,并制訂我國的空域使用管理法規。
記者:目前,也有人擔心,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后,私人飛機的飛行會增多,是否會出現私人飛機墜毀事件?如何利用法律盡量避免這種現象的出現?
劉浩:空域的分類和劃分是一項技術性比較強的工作,空域的類別及四維邊界的劃定相互關聯,必須統籌、科學規劃,不能簡單地認為劃出低空空域就能實現通用航空的發展和私人飛機的自由飛翔,通用航空的發展和繁榮是系統的工程。
空域管理體制的改革已經列入國民經濟“十二五”發展規劃,希望在國家空管委的領導下,盡快研究制訂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空域管理體制、機制,并通過立法體現、鞏固改革成果。但是,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考慮到我國國土防空形勢和我國現有空域監視能力,因此改革目標的實現過程應當是審慎的、有步驟的。
私人飛機墜機事件不僅給機上人員帶來傷害,還可能給地面、水面上的第三人和環境造成損害,必須加強飛行的安全管理和損害賠償制度。在安全管理方面,法律能夠做的主要包括:嚴格航空器適航管理和飛行執照管理;制訂適當的通用航空經營審批和非經營性登記制度;修改完善飛行規則;明確管制部門、空防部門、其他服務保障部門和飛行人員之間的責任分工;健全事故和事故征候調查機制;嚴肅違法違規飛行處罰制度。在損害賠償方面,法律一方面要將通用航空的第三人損害賠償保險列為強制保險,另一方面還要建立并不斷完善第三人損害賠償保險理賠制度與程序。
記者:有觀點認為目前我國航空領域的法律缺乏支架性法律,這嚴重制約了我國航空業的發展,您對此怎么看?
劉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非常重視各行業領域的支架性法律,盡管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建成,但在航空領域仍然存在著支架性法律的缺失。由于缺乏能夠統一調整國家航空(包括軍事、海關、警察和其他國家勤務飛行)和民用航空的支架性立法,許多航空領域的深層次矛盾無法解決,或者說無法根本、徹底解決,例如航空管理機構、空域管理體制等,諸多矛盾的解決往往取決于部門協調和領導批示,制約了我國航空事業的發展。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法》歷經4年,已經形成了兩個較為成熟的版本,并進行了大范圍的調研和意見征求。據了解,今年年初召開的國家空管委全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法》草案進行了審議,有關機構正在按照空管委全會的決策積極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法》的立法進程。
記者:您在前面提到,美國的通用航空器達23萬架,在像美國這樣通用航空比較發達在國家,有哪些立法管理經驗可以借鑒?
劉浩:首先,國外對私人飛機并非完全放開,也有嚴格的適航、飛行計劃批準制度,就連通用航空最發達的美國在“9·11”之后也開始反思和調整其通用航空的管理制度。
在通用航空比較發達的國家,空域實現了功能導向性的分類管理,采取了靈活調配的機制,飛行計劃的審批制度設計較為合理,凸現了管理的高效和人性。
目前我國的空域分類、劃設和管理制度以及通用航空的飛行管制改革,包括大家最關注、曝光頻率最高的“低空空域管理改革”,都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